|
机制演变:从基础元素到多维设计 2003年,腾讯推出QQ等级,“挂QQ“成为一代网民的集体记忆。 2014年,微信步数上线,朋友圈晒步数与好友比拼成为新的社交日常。 2016年,蚂蚁森林问世,用户通过低碳行为获得环保徽章和植树证书。 QQ等级所象征的积分(Points)、蚂蚁森林成就所代表的徽章(Badges)、以及微信步数所体现的排行榜(Leaderboards),这三大元素合称为PBL,是应用最广泛的游戏化机制,其成功源于抓住了人们的原始驱动力: •对即时反馈的追求(积分) •对社交地位的渴望(排行榜) •对身份认同的重视(徽章) 2017年,游戏化专家周郁凯(Yu-Kai Chou)在其著作《游戏化实战》中提出了八角行为分析法,模型从八个角度分析用户的行为动机,如今,八角模型已成为最广为人知的游戏化框架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产品设计与体验优化中。
八角行为模型 时至今日,游戏化机制已从最初的PBL,衍生出更多创新元素和机制,并被整合到各类应用、平台和企业服务中。
八个核心驱动力的对应机制及示例 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游戏化机制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硬件和AI 的发展,推动着游戏化设计朝着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方向不断演进。
不同世代的游戏化机制偏好 游戏化机制的演变不仅受到技术发展的推动,同样也深受不同时代人群的影响,当Y世代的闲暇时间被KPI与生活切割成碎片时,他们更在乎清晰的进度与明确的目标,而Z世代追逐的盲盒与装扮,在X世代眼中可能只是“花里胡哨”的无用之物,每个世代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心理需求,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游戏化偏好:
不同世代的游戏化机制偏好 不同世代的游戏化偏好不仅反映在机制选择上,更具体地体现在游戏类型的选择中,这些差异进一步塑造了游戏化设计的方向。
TGI:用于反映目标群体在特定行为或偏好上与总体相比的相对强弱的指标。 游戏化设计中的心理机制 人们对于各类游戏化机制的开拓和运用,旨在希望通过影响用户的心理动机,进而引导其行为,无论是通过损失厌恶促使用户保持活跃,还是通过从众心理增强社交互动,这些机制都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用户的决策与行为。 良好的机制不仅能帮助企业实现短期的行为转化(如购买商品、提升活跃度),还能在长期中建立情感连接,增强用户的忠诚度和参与感。 我们的决策往往源于本能和情绪,而非理智。 ——《认知觉醒》周岭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移动营销中的游戏化及其规制研究—李宣 心理捷径:由惯性思维引发的下意识行动,如选择最显眼的选项或默认设置。 启发式:我们基于经验的快速判断,如“限时必定更划算“或“稀缺的一定更好“。 禀赋效应:我们拥有某物时,往往会高估其价值,例如虚拟物品和各类成就徽章。 心理账户:人对不同收入的感受不同,如工资涨100元觉得少,抢到10元红包却觉得多。 感官认知偏差:通过感官影响人的决策,如显眼的字体、华丽的特效、逼真的音效。 最好的游戏化设计,从不是强迫玩家留下,而是让他们忘记自己正在“被设计”。 业务融合与用户初始动力的平衡 不同企业采用游戏化的目的往往存在差异,即便同一家企业,其游戏化目标也会因时而异,决策者在制定游戏化策略时,需要考量两个关键因素: 一、实现业务内容与游戏化机制的无缝融合,形成自然统一的体验。 优秀的游戏化设计不是生硬地将游戏元素叠加在业务流程上,而是需要思考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游戏化与业务融为一体时,用户不会感到这是被强行添加的外部机制,而是体验到一个完整、连贯的系统。 代表案例:记账城市—用消费记录构建专属城市 作为一款记账应用,记账城市将游戏设计与核心业务进行了深度融合,用户在应用中记录的每一笔消费,都将转化为城市建设:餐饮消费催生特色餐厅,购物支出建造时尚商场,教育投资兴建知识学院......此外还有居民角色、成就体系与周期性挑战,共同构建了多层次的游戏化激励机制,让财务管理变得有趣且富有成就感。 Google Play2017 年 “最佳日常必备应用” 、2018 年 “最佳生活助手应用” 2018年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传达设计奖
记账城市 二、根据用户初始动机调整游戏化机制强度,达成动机与机制的平衡。 用户初始动机是指人们开始某项行为时的内在动力,面对需要长期坚持的行为(学习、健身),适度的游戏化设计能有效激发参与热情,缓解过程中的枯燥和痛苦感。反之,用户动机强烈的行为中(如刷视频、看小说),过度叠加游戏化元素反而可能带来干扰,甚至引发厌烦情绪。
行业属性与游戏化机制匹配模型 争议、误区与挑战 2011年,著名的游戏设计师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发表了短文《“游戏化”是胡说八道》,而后又在2015年以长文《为什么“游戏化”是胡说八道》进一步阐述其观点,他认为: 游戏化这一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营销噱头和商业策略,通过简化游戏的复杂设计流程,套用积分、徽章、奖励机制等游戏元素来操控用户行为,舍弃了游戏的自主性和艺术性。 十年后的今天,Ian Bogost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同样适用于当下的游戏产业:大量粗糙滥制的同质化小游戏、以及诸多陷入标准化、套路化的3A产品(如刺客信条系列),这种流水线式的游戏生产模式,正在不断消解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本来价值。 对游戏化的争议不止在学术界,2025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个别企业利用抽奖转盘等游戏化机制,通过虚假奖励诱导用户冲动消费,单日流水高达20亿元,类似滥用游戏化设计的行为并非个例: 2019年,趣步APP被立案调查,该应用以“走路赚钱”为噱头,吸引了超过9500万用户注册,其界面不仅酷似手机游戏,更在其中植入金币、排行榜、等级奖励等游戏化元素,诱导用户持续参与。 2020年,Robinhood(详见报告案例部分)被监管机构指控使用游戏化设计(如炫彩界面、虚拟礼花、进度条激励等)诱导散户高频交易,并将投资活动包装成“可能获胜的游戏“,最终平台支付750万美元罚款,并移除相关游戏化设计。 游戏化设计本身并非上述案例的根源,更多的问题在于对其价值的误解与滥用,作为该领域的长期实践者,我们对外界关于游戏化的认知误区,感知更为明显,这些误区不仅广泛存在于企业决策层面,也普遍存在于行业观察和媒体报道中: 过度强调游戏化的作用 伴随着游戏化机制在各个行业的广泛应用,媒体和从业者在宣传游戏化案例时,往往不自觉的过分夸大其作用,例如在《游戏改变世界》一书中,作者将英国卫报的一项调查作为游戏化案例: 《调查议员的开支》是英国卫报在2009年发起的众包调查项目,邀请民众共同审查22万份议员开支发票,项目吸引了2万多名志愿者参与,分析了超过17万份文档,最终导致28名议员辞职,4名议员被刑事调查,数百名议员被勒令偿还总计112万英镑的不当报销款。
《调查议员的开支》页面:展示当前文件总数、参与人数以及审查进度 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项目,且在项目中使用了游戏化元素,如进度条(展示当前审查进度)、排行榜(展示突出贡献者)、成就/徽章(展示最佳个人发现),但问题是,是游戏化决定了该项目的成功吗? 民众的反腐诉求、低门槛的参与方式、追回公款带来的成就感,以及卫报的影响力和组织能力,共同决定了该项目的成功,游戏化元素在其中只是辅助手段,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将项目的成功都归功于采用了游戏化机制,并夸大其作用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逻辑推演: 如果我们认为是游戏化主导了一个项目的成功,那它也必须为项目的失败负责。 类似的案例还有每年的集五福、以及电商平台在双11、618推出的各类营销游戏活动,这些案例都广泛使用了游戏化机制,且被媒体普遍冠以游戏化的名义,但若只是强调游戏化策略的成功,却忽略了企业庞大的用户规模,以及巨额的奖励,显然是对其成功要素的片面解读。 |

以多维视角洞悉小镇中青年真实的生活变迁,从城乡两栖生活到个体价值的重建,从线下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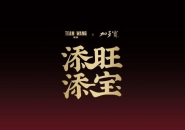
1月9日,国民凉茶品牌加多宝,携手多元时尚高街品牌TEAM WANG design,推出加多宝 ×T...

拉斯维加斯当地时间1月5日,吉利汽车集团宣布基于其首发的WAM世界行为模型,吉利全域A...

在2024CIS特种肥料发展大会期间,四川络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签...

2025年12月28日,由中国制造强国年会组委会、中制智库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制造强国年会在...

2026-01-10
2026-01-09
2026-01-09
2026-01-09

